痖弦先生去世了。他的诗没有去世。他很多年前就写下了那些。他写下它们,然后做别的去了,他没有自己费力去推销,他相信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不胫而走,诗有自己的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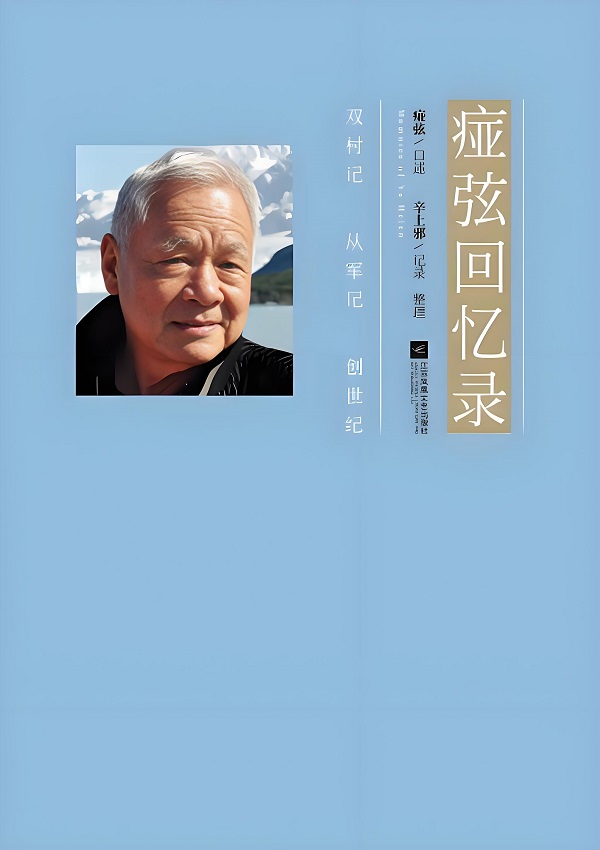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读到了《创世纪》那些诗人的作品,发现新诗天才并没有绝种。还有校园歌曲、三毛的散文,我在大学时代,受到影响。这是抒情、忧郁、感伤、低调、消极、浪漫、波西米亚气质的文学。有助于人生、爱情的文学,好的汉语。在我青年时代的语境中,这种汉语是过于温暖了。
痖弦的诗令新诗有了一种古典气质,他不是抒情诗人。他创造了一种他个人的声音。新诗要么还在八股文的阴影中新瓶装旧酒,要么是味同嚼蜡的翻译腔。痖弦用第三种汉语写作,令古典汉语和现代汉语有机结合,优雅而具有质感。我最近读他的散文《痖弦回忆录》,非常感动,大巧若拙,第一流的文字。
他写得很好,我心仪之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作品不好发表,囊中过于羞涩。朋友给我一个《联合报》第十四届小说奖的征文启事,就手抄投稿过去。《坠落的声音》居然获奖。后来发现,评委都是大诗人,包括痖弦、商禽、洛夫等。后来《创世纪》又颁给我“《创世纪》四十年新诗奖”。有一天,我不在家。年近七十的洛夫先生,到昆明来找我,提着一个青铜奖座(重两公斤),将奖金(当时对我是一笔巨款)和奖座交给我家人。回到家,洛夫已经走了,我无言良久。这种为人对我是很陌生的,犹如回到了《世说新语》的时代。他们带来了一种失落已久的诗教传统。
后来在台北与痖弦先生见面,人谦和儒雅,话不多,声音好听、低调。主编张默先生做东,《创世纪》一帮人请我吃饭,一定要我居中而坐,作为晚辈坐在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师、大诗人中间,我诚惶诚恐,至为感动。就像是与《尚义街6号》或《他们》的朋友初见。我深刻地感觉到那种久违的东西,诗人与诗人之间的肝胆相照、惺惺相惜。
2008年,诗人陈黎邀请我去花莲参加诗歌节,痖弦、杨牧、吴晟、马悦然等都去了。我们谈论了余光中的诗。杨佳娴知道我写字,去当时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“颜真卿真迹展览”买了一本颜真卿的画册送我。书生模样的陈义芝带我去买毛笔。在松园别馆举办一个小的摄影展,那张在越南拍的少女在列车窗前张望的海报我很喜欢,离开时去要,已经被痖弦要走了。有个夜晚我们坐在松林别馆外面的池塘边,听一位诗人弹琴唱歌。
诗是一种生活,也是一种为人。
声明:本网转发此文章,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,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、消费建议。文章事实如有疑问,请与有关方核实,文章观点非本网观点,仅供读者参考。









